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刘晓波:昨日丧家狗 今日看门狗-透视当下中国的“孔子热”
Liu Xiaobo: Evil of Confucianism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02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作者:刘晓波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 更新时间:9/1/2007
中国人热炒大国崛起,由经济崛起发展为文化崛起,由满世界撒钱到软实力输出。在国内,继“读经热”、“祭孔热”、“儒教热”之后,央视“百家讲坛”掀起“读孔热”,为了重建中国的道统;在海外,中共投资大建“孔子学院”,为了向外输出软实力。一种压抑百年的天下心态的发泄,让孔圣人在海内外连成一线,“孔子热”愈演愈烈。
在这种热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崇圣传统的复活,是官方主导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因为,六四后,官权一方面奉行的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另一方面主导和煽动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配合着官方的“小康盛世”之喧嚣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比如,《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的结尾写道:“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就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福音的双重奏的典型文本。
最近一年,央视“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掀起了风靡全国的“于丹热”。一方面,电视传媒成功地把孔子时尚化商业化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摩登孔子”), 如同前些年毛泽东的时尚化商业化一样。有关孔子的各类书籍已经变成书业中高盈利品种,各类国学班和读经班也是高盈利项目(比如,清华的“国学班”学费每人26000元,复旦为每人38000元,少儿读经班更是收了天价)。另一方面,于丹讲孔子,是古人大话与流行歌词相混合的语言叫卖,她对孔子的任意而浅薄的解读,为“儒教复兴热”注入通俗化的精神麻醉剂。按照于丹的《“论语”心得》解释的孔子精华,人人都可以在犬儒心态中活得滋润——无论遭遇到什么,只要不抱怨,而是逆来顺受,就能随遇而安,活出幸福。
正当于丹掀起的“读孔热”持续升温之时,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以考据功夫对孔圣人进行了“祛魅”式还原。他在《自序》中谈到自己读《论语》的态度:“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正是基于这样的不崇圣、不媚众的求实态度,李零才会打破绵延二千多年的崇圣尊孔传统。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
李零读《论语》的水平,无论在考证上还是在释义上,都远远超过浅薄而随意的于丹。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李零,对两千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孔子,也颇多感同身受的温情理解。他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因为“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然而,李零的丧家狗之论,犹如投进“孔子热”和“国学热”的大石头,激起儒家卫道士的群情鼎沸,围攻的口水四溢泛滥,甚至不乏恼羞成怒的谩骂。呵斥为“愤青”者有之,判定为“末世论”者有之,有人甚至没有读过李零的书就将其斥为“垃圾”。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李零读《论语》的书名为“丧家狗”。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新儒家对孔子的崇拜,已经到了“孔圣人”碰不得的地步。亏这些当代儒家的手中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如果有,大概又要回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了。
李零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他读《论语》,不是读圣贤书,而是研究历史;他考证出的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一个找不到归属的知识分子。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是拿《论语》当历史研究,不是当崇拜的道具。”其实,李零的“丧家狗”之说,不过是还原了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惶惶然状态。李零把“丧家狗”解释为流浪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而依我看,用“丧失精神家园”来评价孔子都是抬举。事实上,孔子周游列国,并非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为了寻找为权所用的家园。他一心想做“帝王师”而不得,是找不到权力归属的“丧家狗”。如果他当年能够找到重用他的帝王,他也早就变成权力的“看门狗”了。
“丧家狗”的发明者也并非李零,而是古人对孔子的评价,孔子本人也认可这种评价。孔子周游列国跑官,颠沛流离十四载却一无所获,他在极度失望中愤愤地感慨到:“吾道穷矣!”“天下莫能容!”
所以才有后人的“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评价。但在卫道士们看来,孔子自称“丧家狗”是圣人遗训,饱含着种种治国育人的微言大义;而李零称孔子是“丧家狗”就是大逆不道,是不值得一阅的“垃圾”。甚至有“愤儒”直呼“李零老师疯了!”
无论当代崇圣尊孔的儒者们多么鄙视李零的《丧家狗》,但在我看来,李零读出的孔子,特别是那篇平实而出彩的《自序》,已经胜过蒋庆等新儒家关于孔子的所有言说。所以,一些著名学者对《丧家狗》给予很高的评价。
历史学家吴思先生《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 我读〈论语〉》中说:“……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说:“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在访谈中,称赞李零读《论语》的严肃、考据学工夫、消解神圣化和批判精神。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南方周末》2007-07-12)一文中说:“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在有着悠久崇圣传统的中国,古今卫道士眼中的孔子,是不容质疑的圣人,是历代帝王之师,是拥有道统至尊的“素王”, 是皇帝们都要叩拜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是被康有为和孔教会尊为“教主”的神,如今又被新儒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孔子说的每句话,既是治国醒世的箴言,也是修身养性的指导。最夸张的说法,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今天有“孔子上管5000年,下管5000年”之论,更有“不读孔子,无以为人”之说。当代儒家甚至不惜编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而且是借洋人以自重的假新闻:1988年世界各国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群聚巴黎,公选孔子为世界第一思想家。
面对拜圣者的走火入魔,恕我对当代儒家说句糙话:在你们眼中,孔子既然已经成圣,那就放个屁都沉甸甸、香喷喷。崇圣者已经迷失到分不清家常话和微言大义的区别,把《论语》中的家常话当作微言大义来读。比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家常话,有什么微言大义,犯得着浪费那么多智慧注释两千多年、至今还在注释吗?正如周作人在《论语小记》所言:“《论语》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德国大哲黑格尔也认为《论语》不过是常识性的道理而已。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命运,犹如得不到权力垂青的丧家之犬,那么,汉武帝钦定“独尊儒术”之后,孔老二变成孔夫子,丧家犬遗骸就变成维护皇权独裁制度的“看门狗”。由于儒术有利于皇权统治,所以儒家的“看门狗”地位也还算稳固,一坐就是二千多年。而当读书人的偶像被官权捧上了天、甚至变成皇家祖庙里的镀金偶像之时,恰恰是中国知识人及其思想堕入地狱、变成权力的婢女之时。正如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之后悲愤地感叹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直到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大门,传统的制度及意识形态才开始急剧衰落,辛亥革命终结了传统帝制,作为皇权独裁意识形态的儒家也失去了制度依托,再次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尽管,也有过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尊孔大戏,但那不过是过眼烟云的闹剧,因为传统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丧失了权力依靠,是传统儒家的大不幸,使皇权的看门狗变成了流浪狗。但在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读书人从“看门狗”再次变成“流浪狗”,却是中国知识界的大幸。因为,不再依靠独裁权力支撑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流浪狗”命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随着中共极权统治君临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连“流浪狗”都当不成了。大部分沦为被穷追猛打的“落水狗”,少数幸运儿变成毛泽东政权的“看门狗”。比如,在民国时期敢骂蒋介石的郭沫若,却在1949年后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
孔子在现、当代中国命运颇为诡异,先后经历了两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六四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反激进主义的思潮,把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和毛泽东的反传统一勺烩,同样作为激进主义革命加以抛弃,而全然不顾两次“打倒孔家店”的完全不同。
首先,两次反孔运动的发动者完全不同。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民间文化运动,其发动者大都是来自民间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并以西方价值为参照来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于洋务派的器物不如人和维新派的制度不如人,而深入到文化不如人的层面。而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是自上而下的由独裁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其发动者毛泽东不仅握有绝对的权力,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独尊地位代替所有其他的思想——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固有的。
其次,两次反孔的性质完全不同。五四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发起“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革命,针对不是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的孔子,而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孔圣人,是为了打倒作为独裁皇权“看门狗”的儒术。而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没有任何文化诉求和弃旧图新的动机,而完全是基于捍卫自身权力的政治需要。他把批孔作为党内权争的政治工具,既是为了彻底批臭林彪,也是为了警告“党内大儒”周恩来。
也就是说,两次打倒孔家店有着本质的区别:手无权力的新型知识人与手握绝对权力的当代秦始皇之间的区别,自发文化运动与权力操控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区别,为古老中国寻找文化出路与为巩固绝对权力而整肃异己之间的区别。
所以,时至今日,我仍然赞同五四时期作为自发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但我坚决反对文革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打倒孔家店”。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称孔子为“摩登圣人”,也是在批判帝制中国的崇圣传统。他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崇圣传统堪称最大的文化造假工程,由历代帝王和御用文人共同参与建造。被历代帝王和大儒们“封圣”的孔子,早已远离了真实的孔子,堪称最大的假冒伪劣品。
其实,认真读读先秦诸子就会发现,被尊为圣人孔子,实为先秦诸子中最平庸的道德说教者。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没有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缺少大智慧而只有小聪明,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入,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零先生读《论语》的真意,一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发。该书虽为还原“真孔子”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剥去了历代儒家赋予孔子的虚幻圣贤之皮,但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直接质疑“读经热”和“尊孔热”,间接质疑所谓的“大国崛起”。李零眼中的孔子仅仅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是在批判拿孔子当救世主的当代儒家。正如李零自己所言:“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有兴趣。”“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二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总想与权力套近乎的传统,因为现在的儒家正急于与当权者套近乎。他们独尊儒学,呼唤儒教,并非注重儒学对重建国人道德的作用,而是注重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功能,为的是实行政教合一的王道;他们把孔子推上“帝王师”或“国师”的地位,呼吁把儒教定位“国教”,希望政府以行政权力大树特树孔子,实际上是这些新儒家想扮演当代的“帝王师”,进而变成柏拉图式的手握大权的“哲学王”。于是,新儒家重塑的孔子是向汉武帝时代的倒退,意欲再来一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孔子,是在复活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人格神”的传统。
李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满怀乌托邦理想知识分子,只有作为独立于权力的批判力量才是本份,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权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恰恰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李零说:“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很狂妄,自以为“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自许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建立起人间天堂。宋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还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当作座用铭,说明了中国士大夫狂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
正是基于此,李零告诫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必须与权力保持距离,放弃“帝王师”的野心,抛弃把古代经典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传统,以维持知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激发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力。正如李零在《自序》的最后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知识人,仍然象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那样,无法摆脱甘当他人走狗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无人赏识时如同“丧家之犬“,得到垂青时犹如中彩的“看门狗”。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为人间皇权的永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仁治外衣。帝王们当然看得出来这件外衣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也就是如何变成“好奴才”的传统。正如毛泽东对知识人的定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人来说,首要的责任并非维护一种靠独裁权力支撑的崇圣传统,而是摆脱依附权力的御用地位,承续自五四以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新传统。
2007年8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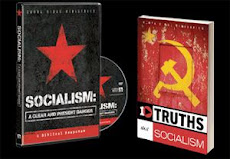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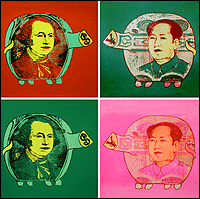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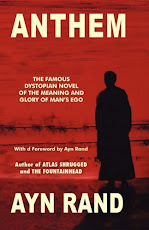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