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Freedom is About Individuals in Society
作者:刘晓波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在朝精英就更倾向于选择“德日模式”,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在野精英更倾向于选择“苏俄模式”,二者共同摈弃“英美模式”。在精英群体中,即便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事实上也没有参透自由主义的精义,他在经济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徘徊于自由宪政和威权秩序之间;他在理论上强调个人权利而在现实政治的选择上强调“好人政府”。"
【书籍下载】Link to Download: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zjjshao/200804/Article_20080411011055.shtml
2/21/2008 1:31:25 PM
当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然而,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
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
序言: 由误入歧途到歧途知反
尽管,经历了二十五年改革的中共政权,在文明模式的选择上仍然拒绝宪政民主,在当下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固守跛足改革的邓小平模式——经济发展与政治停滞的分裂,中国目前在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在根本上源于邓模式的政经分裂。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毕竟出现过双足改革的赵紫阳模式——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并行,这一模式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尽管,赵紫阳模式因邓小平制造的六四大屠杀而中止,但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已经崩溃,中共政权合法性也因六四而严重流失,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的大势之明朗和国内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合力,使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走向,误入歧途的概率越来越小,而迷途知返的概率越来越大。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相及其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级化。
当时,急于摆脱内忧外患的中国精英阶层,面对着外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的两种模式——英美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德日苏的独裁主义模式——两种模式之争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对于开放不久的国人来说,本来就已经很难辩别其优劣,何况,当时西方各国的情况也很复杂,自由宪政还没有完全显露出制度优势。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极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剧了这种残酷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的法西斯主义模式造就了两国的崛起,苏俄模式的崛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接踵而来的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因一战及其随后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而尽显颓态。于是,德日法西斯主义、特别是苏俄共产主义作为成功的新兴革命显示出朝气蓬勃的一面,而西方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步入日暮途穷。初生朝阳与黄昏落日之间的对比,资本主义的黄金梦在西方人自己心中破灭,法西斯和共产的极权体制对自由民主体制似乎具有了道义优势,诸多的西方精英先后转向拥抱苏联模式。
其二,这样的制度对比,自然使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晦暗不明,诸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发生了由模仿英美转向模仿德日和苏联,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国门初开、突然面对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挤压下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本来就在急遽变动的国际局势面前无所适从,难以进行有定见的模式抉择,只能通过不断变换模仿对象来摸索。同时,中国人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浅薄,又与传统帝制保持着深层血缘关系,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遗传性的排斥力,不可能具有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不可能不被席卷世界的“红色苏联热”所裹挟。也就是说,当时的国人,包括大多数精英分子,仍然因袭着沉重的帝制传统,民智未开的愚昧甚至体现在诸多先觉者身上。
平心而论,如果当时的国人不是囿于虚幻性的主观性的情绪性的天朝意识,能够放下“地大物博”和“天下中心”的权力狂妄,而是能够以真实的客观的平等的“交往互利”的国际视野,那么,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比如,面对西方列强的通商要求,当时的日本之处境几乎与中国相同,但应对的心态和策略则完全不同,自然也就导致了天壤之别的结果,在天朝大国眼中的蕞尔小国,开放口岸与西洋通商,全盘西化以学习西方,以明治维新完成制度转型,居然迅速崛起为东方大国,并被西方诸国接纳为列强之一。而曾经是日本榜样的中国,却在通商上被动忸怩,在学习西方上舍本逐末,在内在改革上保守僵硬,中国当时遭遇的民族主义危机,表面上来自列强的入侵,实质上来自政权的内在恐惧,民族主义实质是政权至上主义,以防止社会失序、天下大乱的借口而拒绝内政改革的“秩序党”,骨子里绝非对民族利益的珍视而是对政权崩溃的恐惧。所以,有如此自私、僵化、短视的统治阶层,泱泱大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正是基于天朝意识及其民族危机的原因,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其他民主党派,也无论是倾向西方模式的精英还是倾向苏联模式的精英,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地道的自由主义群体。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在朝精英就更倾向于选择“德日模式”,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在野精英更倾向于选择“苏俄模式”,二者共同摈弃“英美模式”。在精英群体中,即便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事实上也没有参透自由主义的精义,他在经济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徘徊于自由宪政和威权秩序之间;他在理论上强调个人权利而在现实政治的选择上强调“好人政府”。
同时,国家机会主义又使中国的精英以“有奶便是娘”的心态对待外部势力,特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局势之下,当中国的民主启蒙受到内部的重重阻力而难以为继时,中国精英转向一种以现代性包装的伪新潮就是必然的。以至于,对立的国共两党却朝拜同一尊菩萨:苏联的政党模式。苏联所扶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寻求英美帮助未果的孙中山也转向了苏联,按照列宁政党模式对国民党进行了全盘改造。尽管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更倾向于德国的法西斯模式,但作为政党的特质而言,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正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也!
中国的现代化经过进一步、退两步的折腾,最终还是误入“苏联模式”的歧途,传统的家天下变成了现代的党天下,官权独裁和民权空白的社会格局依旧。以至于,在世界大势已经明朗的今天,中国现代化仍然在中共政权的操控下,蹒跚在“技术模仿而制度拒绝”的“洋务情结”之中。对此,已故的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将之概括为“后发劣势”,其结果就是政治独裁下的“坏资本主义”而不是宪政民主下的“好资本主义”。以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为核心特征的“坏资本主义”,不仅使现代化的优先目标“人的解放”无法兑现,而且带来了腐败横行、贫富分化加剧、道德荒芜、环境破坏、政权的合法性和施政效率的急遽流失。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种“坏资本主义”走下去,很可能把中国引上崩溃之路。
习惯于本土帝制传统的中国精英,在苏、美两大模式进入势均力敌的冷战之后,也就必然更倾向于苏联的极权现代化:误把现代世界上最空洞的共产乌托邦当作人类的终极理想,也把最野蛮的极权体制当作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内外因素的结合,将中国的变革引上了完全错误的方向:中国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内在的自觉,而是来自外在的逼迫;变革的目的,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变革的路径,不是民间自发争取主人地位的权利运动,而是寻找新救主拯救的造神运动,也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极权化。所以,外部环境的晦暗和内部环境的蒙昧的共同作用,将中国的现代化引向歧途。
斯塔尔夫人曾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共产极权正是最现代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它为人类描绘的乌托邦之完美及其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官僚体制的力量,它对人的控制和剥夺之彻底,它所制造的人权灾难之残酷,都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实施的强制洗脑,不但泯灭一切异见和多元化的价值偏好,而且把人逼入绝对愚昧及其对极权者个人的崇拜狂热之中;它所实施的强制阶级灭绝,不但要消灭公开挑战的政敌,而且消灭政权的信徒和决不会惹是生非的顺民;它提倡的斗争哲学,煽动起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仇恨和撕咬,充分释放出人的破坏性和纵容人的弱点,在道德上把人性变成兽性。
本来,斯大林暴政的惨无人道和效率低下,在三十年代实行的“大清洗”和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已经使苏联模式的致命弱点开始暴露,内部危机也开始显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延缓了苏联模式危机的全面爆发,也延缓了人类对苏联体制的批判性清理。二战结束后,依靠武力输出,苏联模式全面占领了东欧;依靠意识形态劝诱和武力援助,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从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帝国。然而,这使极权统治达至顶峰的胜利,也意味着衰弱的不可避免。斯大林死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不仅来自西欧,也来自苏东集团的内部。在苏联,赫鲁晓夫以极为激烈的态度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极权罪恶,接着是勃列日诺夫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东欧,先后发生过“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团结工会”等反极权运动;在南斯拉夫,铁托独裁的叛逆者揭示了“新特权阶级”的制度现实;即便在极权者的威望仍然如日中天的中国,也有1956年爆发的对党天下的批判;这一切,逐步揭去了苏联模式的红色伪装,全面暴露出共产帝国的邪恶及危机:经济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危机,政治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危机,信仰上马列主义的危机。西方的左派们也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优越性。在此全面危机中,要么改革、要么死亡。东欧国家内部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化,改革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东方模式的核心支柱苏联本身也开始摇摇欲坠,不得不进行“公开化改革”。
然而,东欧集团和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反省,在中国造成的却是相反的效应,赫鲁晓夫开创的“解冻时代”,在毛泽东眼中,非但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因为反对个人崇拜对极权具有颠覆性。所以,毛泽东认为由他本人争夺共产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方面,他公开与苏联决裂,对外开辟了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并自奉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对内开始了一系列把绝对极权和个人崇拜推向高峰的运动,直到“文革”的极权大灾难,才使国人又一次醒来,面对自身的落伍、僵化和衰弱,开始了有限改革。
概言之,1848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整整百年的现代化努力,历经曲折、教训多多,但最终还是误入歧途,且是误入了最大的歧途——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共产极权。好在,人为不行,还有天助,毛泽东的过于疯狂,也导致了极权的过于短命,随着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中国又重新开始了又一次迷途知返的现代化努力。虽然,后毛时代的中共,一直奉行邓小平开创的跛足改革,并为保住独裁权力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致使“坏资本主义”成为主导。所以,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还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正途。然而,当下的中国现代化所处的内外环境,皆达到百年未遇之大好,国际大势的明朗和国内民间的觉醒,正在共同推动着歧途知反的进程。
在外部环境上,半个世纪的东西冷战,终于以自由制度对极权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已经明确:以西方联盟为代表的文明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文明,不但具有充分的道义优势,也具有实现其道义诉求的实力优势,其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使中国变革的未来方向唯有自由宪政一途,否则就仍然走在歧途之上。现在的威权模式仅仅是过渡期而已——尽管这个过渡期比起东欧各国来会长一些在内部环境上,虽然官方仍然坚持维护独裁制度和权贵利益的跛足改革,但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民间,蕴含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强大动力。在清末民初被启蒙精英们无视、甚至仇视的私有产权,经过毛时代走向极端的大公无私,经过改革以来民间的不断推动,现在已经反弹为保护私产入宪的全民共识;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得分化。在经济上,指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趣味日趋多样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坚守权力一元化的僵硬体制,但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蚕食下,体制内也不在是铁板一块,其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一直处在急遽地分化之中。
特别是经过八九运动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教训,人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人权至上正在逐步变成全民争取的目标。在国内外争取人权的诉求和运动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下,合法性极为脆弱的中共政权也不得不开始谈论和正视人权问题,以至于,曾经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的敌对观念的人权,在2004年的中共两会修宪中居然被写进了宪法。换言之,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开明派,基本能够对民意压力作出积极的正面回应,为改革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强大动力,并曾一度主导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并行的大方向;那么,在六四之后的十五年中,党内开明派的缺席和保守派的主导,使中国改革停滞在跛足模式的水平上。但动员广泛的八九运动所唤醒的民意,自发地推动着“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中国变革走向自由宪政的根本希望,就由八十年代的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转向官民对立中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官民之间的现实博弈,也大都遵循着民间的自发扩张和官方的被动应对的逻辑。所有的局部性制度进步皆来自民间自发动力,以及民间压力的点滴积累,官方对民意压力只能在“不得不”的窘境中作出被动回应。所以,权利意识觉醒之后的民间,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逐渐把分散的民间力量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才能催生出更具建设性的民间力量,也才能不断增强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强大压力,进而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故而,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已经成为民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以民间压力推动现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革新,也已经成为当下改革的有效路径。无论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非但无法回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动变革力量——国内体制内外的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
一 中国改革的两种逻辑
一直以来,国内精英和西方舆论,习惯于把中共政权看作改革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往往最关注的是中南海的动向。而在我看来,这样理解中国改革,既是远离事实,也是不公正的。因为,现实中的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执政党的显在逻辑,即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发动并坚持“做大蛋糕式”(效益优先)的跛足改革,用满足被统治者的温饱来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可。但是,官方的改革逻辑潜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1,市场经济与垄断管制的矛盾。旨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变成民间自发追求的目标,这种民间目标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垄断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民间经济,必然要求垄断式管制和行政权撤出市场。
2,私有化及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权力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权畸形强大而民权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实质上变成了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旨在克服社会公正危机的财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绝“强盗式资本主义”。
3,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权腐败,而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民间的最大诉求。这种官民对立使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丧失合法性。
另一条改革逻辑是民间的潜在逻辑,由市场制度和民间自利意识的自发动力构成,它不满足于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张政治和经济、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整体改革。在根本上,当下中国的贫富两级分化的根源,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并非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是源于官权的富足和民权的贫困的制度性不公,没有政治权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间的自发动力所支持的经济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对的是垄断制度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进而要求指向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权的不断扩张和官权的不断收缩。换言之,民间逻辑(私有化及其个人权利意识)乃根植于人性的内在逻辑,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自发地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并以争取民权的诉求对官方逻辑构成挑战和压力。
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显然是官方逻辑主导改革,所谓“邓小平模式”、“江朱模式”、“胡温体制”等表述,就显示着对官方主导的无条件承认。而实际上,民间逻辑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比如:邓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的民意支持;最早开始的农村改革来自农民的自发行动;1992年邓南巡发动第二次改革,显然是为了弥补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他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民间的自发力量推动着改革,官方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有所进展,是官方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动的结果。每一项改革都能进一步唤醒和释放民间力量,民间力量一旦觉醒便不可阻挡,政府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即,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也正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变得更实用更机会主义,它才能对不断加大的民间压力做出灵活的政策调整,也才能在六四后维持住十五年的稳定。
然而,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官方奉行的跛足改革之下,稳定第一和权贵利益优先的改革策略,必然导致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优惠收买,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以边缘地区的日益落伍为代价的,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摧毁伦理为代价的,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和践踏社会公正为代价的。
二 “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的局势
必须看到,强权控制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社会灰色区域不断扩张下的微观稳定,局部繁荣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事实上,对中国现状的相对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强权控制之下,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民间反抗还难以发生,但全国各地的局部反抗却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民间维权的表达空间和组织能力正在得到了飞速提升:
1,农民、失业者等弱势群体要求公平的权利和分配的维权活动,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广东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例外,甚至在政治中心的北京也时有发生。民众的请愿、游行、上访,发动万人签名信,要求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击基层政府,最激进的维权方式是来天安门自焚。三年前,发生在东北辽阳、大庆等地的工运,累积参加人者高达10万人,持续时间将近一个月。现在,许多知识精英和法律界人士加入农民维权,他们为农民提供文字、物质和法律服务,帮助农民公布维权诉求,向外界透露地方政府对农民维权的打压、对维权代表的迫害。比如,律师俞梅荪、李柏光,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等人,一直在帮助福建农民和河北农民进行维权活动。最近,四川万源区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便是最好的例证:仅仅因为一件偶发的公务员殴打民工的事件,就酿成几万名民众围攻区政府的大规模群体抗争。可见,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2,六四后,中国民间的反对运动和人道救助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其发言和行动已经完全公开化。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六四难属,她们见证真相和寻求正义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被誉为“天安门母亲”;更广泛的为六四正名、抗议文字狱和要求政治改革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甚至曾一度出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请愿运动和1998年的民间组党运动等民间反对运动的小高潮。这些纯民间的政治反对动运,尽管遭到现政权的长期压制,但十五年来从未中断过。每年的六月四日,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软肋和心病,令其头痛不已。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便捷的信息平台,民间议政和网络维权表现出持续高涨的趋势,已经成为中共难以有效控制的民间飞地。
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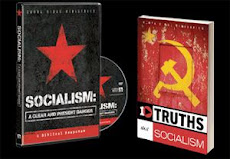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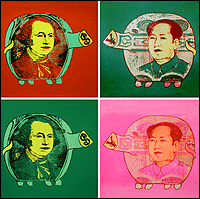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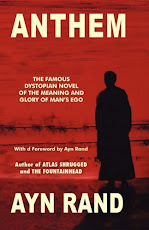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