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Liu Xiaobo interview 2008年就天安门事件采访刘晓波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刘晓波/天安门屠杀与个体责任
Liu Xiaobo/Tiananmen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2010-10-08 14:13 来源: 联合报
(作者:刘晓波,1993年6月5日 )
我们这些被称为「民主斗士」、「民主精英」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只懂书本上、理论上的民主,而不懂实际操作上的民主,不懂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应该如何具体地建立和实施。被称为中国的沙哈洛夫(沙卡洛夫)的方励之教授,在八九抗议运动之前就放弃了这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基本人权的大好时机,他受美国总统布什(布希)之邀参加宴会被阻事件毫无声息地过去了。着名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在八九抗议运动之前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他的「第二种忠诚」。所以,在这样一种连民主的A、B、C、还需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中产生民间反对力量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种现实所产生的八九抗议运动,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空泛诉求。
夸张的使命感和过于宏大的历史感使学生们失去了自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不知道自己那稚嫩的肩膀根本担不起那么沈重的使命。被一次次强化的正义诱惑着学生们以生命、以死亡为代价与政府进行着不断升级的徒劳对抗。似乎只有奉献生命才能打动政府,只有牺牲才足以唤醒民众,只有死亡才能够成就正义,才有资格代表正义。无怪乎当广场的总指挥柴玲成功地流亡国外,有人指责学生们只有激情和勇敢,而缺乏智慧和理性之时,她颇为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在当时的广场,勇气就是水平。」别管现实,拋弃理性,我们只要勇敢,只要肯于献身和牺牲,我们就是八九抗议活动的英雄。
四十年来,我们没有任何民主政治的经验,我们濡目染的全是专制政治的残酷斗争和阴谋诡计,我们一旦革命就自以为唯我独尊,像我们投入文化大革命时自以为自己最革命一样,我们一旦投入八九抗议运动,也自认为自己最民主,何况我们在为民主而绝食、而献身、而牺牲,就更使我们确信我们的行为就是最高的正义,我们的声音就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于是,真理变成了不容质疑的绝对,正义变成了为所欲为和要挟,民主变成了特权,广场成了检验真理、考验意志、锤炼情操、伸张正义、行使权力的万能场所。谁不来广场,谁指责广场,谁就是反民主、非正义、懦夫。一时间,广场似乎成了人人必须过关的试金石。「我在广场待过」、「我去过广场」成了民主意识和社会良知的标志。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不要协调、不讲合作,可以随意拉山头、搞组织,自封为王,高自联、绝食团、对话团、外高联、工自联、知识界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席会、敢死队、飞虎队、西路军、童子军……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满怀深仇大恨,拿着一件血衣控诉万恶的共产党,咬牙切齿地谩骂和污辱别人的人格,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可以声言枪毙╳╳╳,油炸╳╳╳,活埋╳╳╳,可以对非我族类者恶语相加,态度蛮横,甚至大打出手;可以把我们的个人恩怨借正义之名尽情宣泄。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着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
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只要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而强行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我们像当年的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我们也像共产党的警察一样,强迫新闻记者不要拍摄对我们不利的、有损于我们形象的照片,我们野蛮地抢过记者手中的照相机,打开暗盒,让拍好的底片曝光,甚至砸碎记者们的摄相器材。为了不给政府以口实,我们把向毛泽东画像投掷污物的人扭送公安局,致使他们被共产党分别处以二十年、十八年、十五年的重刑。
更可悲的是,八九抗议运动的正义性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要挟。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正义的压力之下沈默了,绝食之举使大学生成了不能批评不允许批评的革命圣人。当人们看到以生命为代价与专制政府相对抗的年轻学生的悲壮之举时,谁还能说出「不」字,谁还敢说出「不」字,绝食使大多数人丧失了理性,使极少数保持理性的人沈默不语。
由是观之,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所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性正义。
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于流血、死人,而且还在于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尽管邓小平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他的南巡讲话又掀起了发展经济的热潮。但是,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畸型发展,赵紫阳的下台使邓小平死后的权力交接成了最危险的火药筒,平稳的权力过渡因深具民心的赵紫阳的倒台而危机四伏,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心理驱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捞一把,民众真切感到邓小平的健在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错过,就会在那死后的天下大乱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双方的恐惧和仇恨都无法消除,而且随着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
因而,结束对抗、消除恐惧、实现社会合作,使中国平稳地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不仅要靠执政党从现在开始的有魄力的自我改造,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且要靠民间反对力量的合作,促其自我改造的渐进完成。能够拯救共产党的只能是共产党自身。逐步地渐进地向民主化的自我改造,共产党则存;而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共产党则亡。同时,社会上的各种民间力量要在共产党还在进行自我改造之时,不是取消它的执政地位,而是促成它在执政时期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有一张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六四」牌非打不可,关键在于怎么打?在什么时机打?我以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发社论,不必开大会,不必公开声扬,只要私下里抚恤「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为因「六四」而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的恢复地位,把靠「六四」之血上台的人逐渐降级、免职,让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安全回国……,如果某位政客在邓小平死后靠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仅是这位政客本人的灾难,也是中国的灾难。突然平反所带来的爆发性后果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六四檔案 - 89)
我不知道,在「六四」血案发生四年后的今天,在「六四」使中国的全面倒退持续了近三年的现实面前,在充满着世纪末恐惧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的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们,是否会从心底里产生深重的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是否能够理性地,平静地、公正地、现实地评估我们在八九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否能够正视目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现实而拿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具体的智慧,切实的设计、从一点一滴做起的耐心。如果能,即使我们只有微薄之力,「六四」的血也没有白流,它仍浓于水。如果不能,「六四」的血不但只是白水一杯,而且至多能供养那些吸血的无耻者罢了。但愿「六四」是中国的最后一次人皆自以为是政治家的全民政治!但愿「六四」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盲目的革命正义的大轰动!
(本文发表于1993-06-05/台湾联合报/10版/大陆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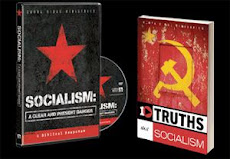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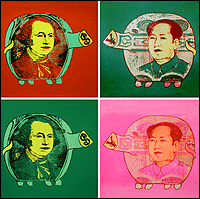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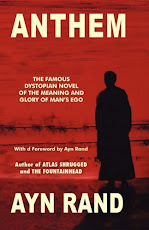










2 comments:
如果抛开了个体的责任,八九天安门前学生们就算得到了他们所要的权力,但缺乏自身的高度自律和理性,那他们也只会成为新一轮的独裁。革命,在屠杀和抗争过程中,绝对需要坚守良知下的智慧和理性。我看到,在长期受这种垃圾文化腐蚀,个个绝顶爱国人人绝对真理的前辈、在鲜血染出的神圣正义感面前,坚守良知与理性,显得太艰难。
我很鄙视我的父辈和我的祖辈,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为害者,他们的愚蠢一再提醒我不要选择走他们同样的路,不要害人也自戕。这个国的国民,死了的活着的都应该深深忏悔他们当年犯过的罪和现在正在犯的罪。包括我自己。
Post a Comment